■人物檔案
馬騁博士于2004年獲得北京清華大學電子工程學士學位。自2004至2006年,馬騁在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進行碩士學習。
自2006年,馬騁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電氣工程系進行博士學習,師從著名光傳感專家王安波教授,并于2012年獲得博士學位,研究主要圍繞白光干涉儀、吸收光譜以及光機諧振器在傳感領域的應用展開。
2011—2012年,馬騁作為技術負責人帶領團隊在美國國家能源技術實驗室成功進行兩次傳感器現場測試,成果獲得國際同行一致好評并受邀參加能源部年度報告。
自2012至2016年,馬騁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生物醫學工程系進行博士后研究,其合作導師是現就職加州理工學院的國際著名生物光子學專家汪立宏教授。博士后階段,馬騁博士的研究主要圍繞復雜介質內電磁波傳輸以及深層組織生物光子學成像展開,所涉及到的核心技術包括光聲計算斷層成像以及激光波前工程。馬騁在其任博士后研究助理階段多次參與、主持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美國能源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項目。
2016年5月至今,馬騁博士以助理教授身份受聘于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組建生物光子學實驗室。他目前的研究興趣包括復雜介質中電磁波傳輸,光子—聲子耦合作用在生物醫學中的應用,光聲顯微及計算斷層成像,激光波前整形及自適應光學,深層生物組織光學成像、治療,以及光遺傳學。馬博士目前已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6篇,包括《自然》子刊兩篇(Nature Photonics,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學》子刊一篇(Science Advances), 以及國際光學學會旗艦期刊Optica三篇,并參與編寫國際學術著作一部。在博士后研究助理階段,以共同項目負責人身份成功申請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2016年,獲得中組部“青年千人”專家稱號。
早春二月的陽光透過窗,灑在清華大學羅姆樓的一間辦公室。光的漫散射映得這間略顯狹小的屋子格外明亮,讓人心生暖意。馬騁就在這里辦公,他是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的助理教授,去年作為“青年千人”剛剛回國。
馬騁的書架上擺著《病理學》《內科學》《外科學》以及其他厚厚的醫學典籍……這種奇特的組合,是否有點讓人不明就里?電子工程系,醫科教材?
其實,這跟馬騁的研究方向有關,他主要從事生物光子學成像,特別是深層組織光子學成像的研究。生物醫學光學成像是研究應用的重要方向。馬騁開展光聲成像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讓醫生或生物科研工作者獲得一種新的觀察生物組織的能力,更強大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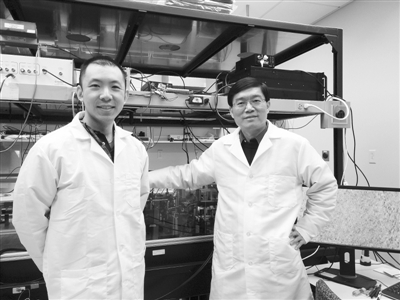
馬騁與合作導師汪立宏(右)合影
打破極限,用光子學手段探測生物
“生物光子學,通俗點說就是用光子學的手段去探測生物。”馬騁向記者開始介紹起這門年輕學科,“如果用光進行成像,我們會得到非常多的信息。從海量的信息里提取我們想要的部分,怎么去看病灶,如何去分析,這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部分。”
生物光子學應用有兩個大方向,一是生物學上的成像,另一個就是醫學成像,用于臨床。臨床上生物光子學普遍用于病理研究時,把組織做切片在顯微鏡下面看,顯微鏡就是生物光子學的設備。
梳理顯微鏡的發展史我們知道,從最早簡陋的光學顯微鏡到如今各種先進的光子學顯微鏡,以及利用生物熒光標簽等手段,為生物學打開新視野已立下汗馬功勞。
光子學成像有其獨特優勢。馬騁講道,首先光的波長相對較短。由于成像分辨率與波長相關一般是正比,波長越短分辨率越高,所以光子學成像可以做到高分辨率。
光學顯微鏡分辨率的極限曾被認為是200納米左右。而獲得2014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超高分辨率熒光顯微技術,則通過一系列物理原理和化學機制打破了“衍射極限”,把光學顯微鏡的分辨率又提高了幾十倍,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視角觀察生物微觀世界。
第二,光的波長能引起能級之間的躍遷,這意味著我們通過光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與分子相關的信息。第三,光電子技術,包括通訊、傳感等近年來發展迅猛,對生物光子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
生物光子學,由生命科學和物理科學交叉融合形成,使生命科學直接深入到物質結構的深層次,并由此帶動了生命科學的深度發展。
進去是光,出來是超聲
光子學有兩大極限,一個就是“衍射極限”,但這已被突破;另一個就是散射極限,它阻礙著光子學探測的穿透深度。這一屏障正等待著科學家們攻克,馬騁就是其中之一。
“光有很多好處,但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散射。”馬騁說,看云、看霧,我們都看不穿,這就是因為散射。光子學只能看到一些表淺的東西,比如說病理切片。由于散射的限制,光子能夠穿透的深度一般也就一毫米。馬騁的目標就是“看得更深些”。
當我們用手電筒照手掌心,可以看到光是能夠透過的,只是量少了很多。“光其實能夠穿透很深,問題是傳播方向變了。”馬騁邊說邊用手比劃。光被散射之后,傳播方向就隨機變化,導致無法用其成像。
但是,超聲可以!如用激光照射一杯牛奶,牛奶會被激光點亮,但是這束激光無法再形成一束激光出去。但光的能量被牛奶吸收,就會生熱,生熱就會膨脹,這一過程會產生超聲波。超聲信號在生物組織中,基本上就是走直線,“我們可以通過檢測超聲來成像”。
這就是生物光子學中一個獨特的研究方向——光聲成像。這是近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生物醫學成像方法。當脈沖激光照射到生物組織中時,組織的光吸收域將產生超聲信號。這種由光激發產生的超聲信號被稱為光聲信號,攜帶了組織的光吸收特征信息,通過探測光聲信號能重建出組織中的光吸收分布圖像。光聲成像從原理上避開了光散射的影響。
光聲成像使深層組織光子學成像前景無限,馬騁在國外求學時在這一領域取得過突破,這也是他回國后科研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
成長之路: 原點、起點和小目標
清華是馬騁的原點,在清華大學讀本科時,馬騁修的是光電子專業,如今又回到母校回到本系任教;十年來,他歷經海外求學、任職、回國,清華又是馬騁的一個起點。
2006年,馬騁赴美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攻讀博士,師從光電傳感界的“大牛”王安波,主要從事光纖傳感的研究。2012年,馬騁博士畢業后到華盛頓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主攻生物醫學光子學。
關于求學歷程,馬騁說一開始對物理很感興趣所以就學了光電子,因為光電子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物理現象;光纖傳感中不僅有很多的物理知識,也跟實際應用聯系緊密,感覺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可以做。后來,馬騁對光電子在生物醫學領域的應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于是果斷地進入了生物光子學領域。
馬騁在華盛頓大學汪利宏教授團隊進行博士后研究階段所負責的波前工程與光聲成像項目是生物光子學領域的前沿方向,他的工作集中在利用光與聲的相互作用在復雜介質內聚焦以及成像,其工作在《自然》雜志新聞特寫專訪中被報道。他和所在團隊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探索,取得了豐碩成果,其結果發表在了2014年12月的《自然—光子學》以及2015年1月份的《自然—通訊》雜志上。
2016年,獲得國家“青年千人”計劃支持,馬騁回到了闊別十年的北京。
“現在政府的政策非常好,鼓勵科研工作者去創新。當時在國外時就想著回國挺好,真正回國了之后,與國內的學者一塊交流、在這個環境里開始奮斗的時候,你會發現比想象的還要好。”目前,馬騁還在組織建設團隊和實驗室,“擼起袖子加油干”形容他的狀態再合適不過。
“從事生物光子學要求對個人的知識體系有極大的擴充。我現在不斷的學習,感覺在生物學和醫學方面,自己的知識儲備還很不夠。我們很多工作要和生物學家、醫生合作,自己需要和他們有共同語言,才能更順暢的交流,把好技術恰當的運用到更多的領域。”于是在馬騁的書架上擺上生物、醫學書籍就很合理了。
出于科研需要,更出于個人興趣,馬騁為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在某幾個專攻領域能像醫生那樣給人看病。馬騁曾經問過一個學醫的朋友,說我想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怎么做?朋友說,比較困難。
“但我覺得短期是比較困難,但這是一輩子的事,可能學個十年二十年,不斷的積累。”馬騁目前跟一些醫生合作搞研究。“跟什么樣的專家合作,就可以學到什么樣的知識,加上自身不斷努力,日積月累或許至少可以當半個醫生了。”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業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文章內容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