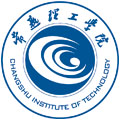■本報記者 甘曉
11月27日,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邱仁宗在發言中對“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予以強烈譴責:“這種行為遠遠低于我們能夠接受的底線,也是最不道德的。”
那么,法律法規在倫理監管中如何發揮作用?當前的倫理監管存在什么問題?我們應當從這一事件中反思什么?為此,《中國科學報》專訪邱仁宗,詳細剖析了上述問題。
《中國科學報》:歷史上,全球范圍內,有沒有像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這樣嚴重違反倫理的科研?它產生了什么影響?
邱仁宗: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重視對科研的監管。那時揭露了一些丑聞,最嚴重的莫過于一項在政府公共資金支持下,對黑人梅毒患者進行的長達40年的研究。該研究對受試者不給藥物治療、沒有知情同意,對病人說你得了“壞血病”,每天抽血做檢驗,目的是全程觀察患者在不加治療的情況下,病毒最后侵害大腦還是心臟。
丑聞被揭發后,總統生物醫學研究和行為研究委員會建立起來(后改名為總統生命倫理學顧問委員會),發布了《貝爾蒙報告》,并于1981年制定了由聯邦政府16個部門簽字承諾執行的《共同法則》,又稱《聯邦監管法典》。
《中國科學報》:據我們所知,這是美國率先把對受試者的保護及倫理委員會的規定制定成法令的形式。那么,這部法令規定了什么?
邱仁宗:《共同法則》要求對涉及人的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進行倫理監管,成立由非本研究成員組成的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對研究方案進行外部倫理審查。同時規定研究人員獲得記錄和知情同意,規定對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成員、職能、運作和審查的要求,并對包括孕婦、體外受精者和胎兒、囚犯、兒童等某些弱勢受試者予以特殊保護。
《中國科學報》:我國目前就保護受試者已經出臺了哪些規定?在你看來還存在哪些欠缺?
邱仁宗:我國已經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機構陸續頒布保護受試者的管理辦法和規章,各研究機構也建立了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研究方案。
但我們缺乏一個專門的行政機構來對這些規章的實施進行監管,使這些法律法規最終流于形式。對此,可借鑒國外的做法,規定凡從事科研的單位必須建立保護受試者和科學誠信兩個辦公室,沒有能力建立這兩個辦公室的不能進行科研。
另一個缺陷是沒有問責和罰則的條款。對違反這些管理辦法和規章的相關個人(行為人)、所屬單位、所屬省市的相關行政管理部門(以及省市的倫理委員會)沒有追責的要求,對違規個人更沒有處罰措施。
《中國科學報》:觀察近年來的科學發展,似乎存在“技術先行、倫理在后”的現象。對此,倫理學應該做什么?應當如何改變這一局面?
邱仁宗:科學的發展依靠的是人的創造力,無法預測誰在什么時候做出什么發明和創新。因此,倫理學不可能做到“事前諸葛亮”,更不能憑科幻小說來制定倫理規范。
倫理學能夠做、應該做的是對創新技術研究和應用的事先防范。例如,對于科學家提出的基因編輯方法,我們不可能事先就給基因編輯的研究和應用制定規范,但當我們逐漸地知道基因編輯的優缺點,基因編輯技術可以用于人、動物,可以用于體細胞和生殖系,可以用于治療、預防和增強,我們就可以形成初步的規范。
例如,由中國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美國科學—醫學和工程科學院聯合制定的基因編輯研究規范中明確指出,允許在人胚胎上進行胚胎研究,但不能超過14天,不能用于生殖的目的;對生殖系基因編輯雖然不能絕對禁止,但必須非常謹慎,滿足一定的條件;對于基因增強,不管是出于醫學目的還是非醫學目的,現在都不應該考慮。
倫理學落后于科學,一方面因為科學發現不可預知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對的,所有的倫理規范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法律法規都是對未來行動的制約。
《中國科學報》:您在此次香港峰會期間接受采訪時用“沒有一個做科研時老想獲得諾貝爾獎的科研人員獲得過諾貝爾獎”評價了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您認為這件事對當今中國科學界有怎樣的啟發?
邱仁宗:我國某些科學家以及管理人員加上追求轟動效應的媒體,往往急切地將獲得諾貝爾獎作為科研目標,這是舍本求末,往往適得其反。
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成就,或者對自然界的奧秘有深入的理解,例如發現基因是具有雙螺旋結構的DNA,或者其發現或發明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例如發現青蒿素。這是需要科學家竭盡他的時間、精力和生命去做的,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諾貝爾獎。
像賀建奎那樣的年輕人,僅僅是生物物理學的背景,沒有受過醫學、遺傳學和生殖醫學系統訓練,也沒有這些方面基礎和臨床的實踐,同時還要管理8個公司,他可以將人家已經發明創新的東西盡可能快地應用,其本身則毫無創新可言。期待用這種方式制造“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大學以及科研管理部門值得深思。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業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文章內容僅供參考。